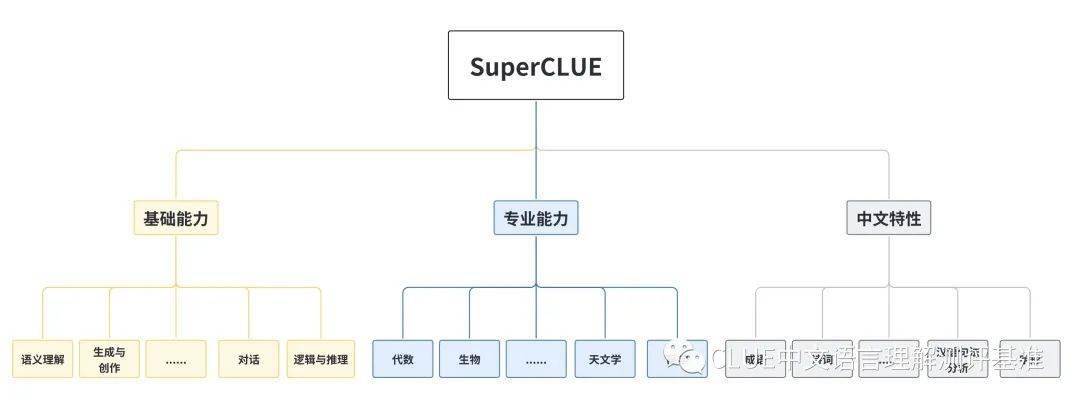《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3.6.26总第109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在一首赠诗里,语言学家刘半农如此勾勒好友黄文弼在沙漠戈壁中的寒酸模样。
在另一首照片题诗里,刘半农又调侃道: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来,我当敬汝一杯酒。
俏皮的言语之下,隐约透露着四伏的危机。
1930年,37岁的考古学家黄文弼终于结束3年多的西北科考,从新疆平安回到北平——他启程的时候还叫北京。他启程的时候,满口牙齿也还健全,如今已经掉了几颗。
“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在北大为他举办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激赞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从此,黄文弼被认作“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此后30年,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黄文弼辗转于北平、南京、西安、城固、成都、峨眉等地,在颠沛流离中,完成新疆考古成果“三记两集”的撰写,为新疆考古揭开序幕。
然而,这几本考古报告,始终是竖排繁体的初版模样,再也没有重版过,后人只能阅读电子版和影印版。正如黄文弼的命运,这位成就斐然而经历奇特的学者,他的故事却少为人知。
时隔75年,黄文弼扛鼎之作《罗布淖尔考古记》近期再版,罗布淖尔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布泊。而另外两本《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也将再版发行。七八十年前,便用洋洋百万字书写了新疆考古全貌的黄文弼是谁?
丈量八万里山河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正雄心勃勃地准备着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辟一条从柏林到北京和上海的新航线,委托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斯文·赫定做一次勘探,同时借此机会对中国西北再做一次科学考察。
自从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激发起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兴趣。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世界文明交汇的中心地带,成为探险热中最迷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晚清内忧外患和军阀混战自顾不暇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西北文物的大量流失,包括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以及西域楼兰等古国的文书、简牍、佛像等,被西方和日本探险者一箱箱、一车车运到海外。
当斯文·赫定带领着欧洲人组成远征队重返中国,虽然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证,却遭遇了北京学术界的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界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其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外团长共同负责,中方派出6名学者和4名学生,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筹集。
西北科考团中方团长为北大教务长徐旭生,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
在后来学生的回忆中,黄文弼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望着他的衣服,不免会联想到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与不修边幅的衣着相映衬的,是刚正耿直的性格,这将在他与欧洲人同行的科考之旅中显露无余。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从北京出发,前往内蒙古。
科考团到达居延海附近时,为了鼓励团员的积极性,中方团长徐旭生建议设立奖励机制。斯文·赫定说,倘若能再发现一座楼兰城那样的古城,赏洋5000元。楼兰城的发现是斯文·赫定平生得意之事。徐旭生笑道:“此话若黄先生知之,定觅二古城,得一万元。”斯文·赫定赶忙说:此话万不可让黄先生知道。但徐旭生转身就告诉了黄文弼,黄文弼一笑:“发现一城不计甚事,余到新疆希冀发现一国耳。”他雄心壮志,希望寻找到西域古国。
黄文弼对斯文·赫定的学识与成就不乏钦佩,但作为经历了五四思潮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文物保护问题,他对瑞典人是铁面无私的。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黄文弼中心副主任吴华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科考团出发之际,黄文弼就将“监督外人”作为重要目的之一,所以处处阻挠外方团员想要开辟航线、私自进行野外考古等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动。斯文·赫定随手在帐篷外插上瑞典国旗,黄文弼马上拔掉,换上中国国旗;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外国团员拍了照,黄文弼上前阻栏,认为“有辱国格”。
1928年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独立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扰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 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
1930年4月,黄文弼抵达罗布泊北岸。4月23日上午,他派出两支猎户组成的小队往附近探寻古迹,自己留在驻地工作。当天下午狂风骤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本地人称这种天气为“黑风”。晚间,大风未息,驻地棚帐几乎被摧毁。黄文弼听着狂风呼号,担心没带皮衣的猎户们,一夜惴惴不安。
次日上午,大风停了下来,但尘沙未减,寒冷异常。一队猎户终于安全回归,带着拾到的铜矢镞等古物。而另一队的猎户拉亦木却始终没有回来。傍晚,黄文弼远远瞥见一人骑着马,身披大裘,戴着皮帽,猎枪横陈在马背上,手执缰绳,从棚帐前徐徐经过。掀开帐幕一看,正是拉亦木。他在考古报告中罕见地喜形于色:“余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
黄文弼整个罗布泊考古中最著名的发现,随着拉亦木到来。
那是一处汉代烽燧亭遗址,只剩西墙的墙基和三根直立的木柱,黄文弼在芦苇草中捡到了数十枚木简,根据木简残文,此地名为土垠。土垠遗址一共发掘出70余枚汉简,比国外探险者在新疆发现的汉简年代都早很多,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首任主任朱玉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工作的任何一次行为,都是不可替代的。譬如,如果不是罗布泊丰水期阻挡了黄文弼前往楼兰的脚步,那么在罗布泊北岸代表着西汉经营西域的土垠遗址,可能至今还沉睡在荒漠之中。对于西汉在西域地区沟通丝路文明交流的认识,也要等待很久,才能达到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所表述的高度——甚至还未必能够达到。
罗布泊地区位于新疆东南部,与敦煌接壤,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散布着大量重要遗址,著名的西域门户楼兰古国就在罗布泊岸边。罗布泊如今自然条件恶劣,但许多重要发现都是在这一地区得到的,如斯文·赫定1900年发现的楼兰遗址,斯坦因在尼雅、楼兰所得大量佉卢文文书,日本大谷探险队所得李柏文书等都著称于世。
黄文弼在土垠遗址的发现,同样十分重要。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说,人们熟知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南北两道,这都是西汉中期的事,汉初从长安通西域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历来没有明确证据。而他在土垠遗址烽燧亭发现简牍和古道之后,“汉初通西域之情形,由此可以确知也。”
离开罗布泊后,黄文弼继续前往塔里木盆地,在盆地中考察了一年半,调查遗址达百处以上,如著名的龟兹、于阗、焉耆、尉犁、危须等古国,都有涉足,还新发现了大量古城。如果斯文·赫定说话算话,黄文弼的奖励恐怕可以拿到好几万大洋了。
1930年9月,完成所有任务后,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他带回了煌煌成果,新疆的采集品有80余箱。整个西北科考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北疆发现了恐龙化石;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和“小河公主”;中国现代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的一万多枚“居延汉简”,也出自西北科考团。
这一次蒙新考察,奠定了黄文弼终身的学术方向,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三次重返新疆。四次西北考察,他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穿越塔克拉玛干
自从离开北京,黄文弼就踏上了风餐露宿的苦旅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壮举,是一介书生,凭借着简陋装备和物资,竟然成功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斯文·赫定曾试图穿越,结果喝光了水,只得喝人尿、骆驼尿、羊血,险些丧命,最终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失败而回。
据《汉书·西域传》及《水经注》记载,塔里木盆地南部有一条“南河”,最终汇于罗布泊。“南河”后来消失在沙漠中,为了探寻这条古河道的遗迹及变迁,黄文弼决定做一次前路未卜的冒险。他由盆地北沿的沙雅,穿过茫茫沙漠,到达盆地南沿,用时1个月6天。结束之时,对于旅途的艰难与惊险,他只淡淡记了一笔:“辛苦备至”。
翻开他的日记,则能具象地体会到所谓“辛苦备至”到底是什么意思。
进入沙漠第二天,黄文弼分析沙漠地形,从沙雅入沙漠到于阗古城出沙漠,800余里沙海,中间地形不明,尤其是至克衣河的400余里中没有任何水草。而且从北往南比从南往北更难,他们走的正是更难的路线,途中必须抵达克衣河补充水分,一旦错过,“必为克衣河两岸沙漠中之白骨”。
如果从高空俯瞰,可以看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西北风吹拂之下,形成一条条如山脉一般的沙山,山与山之间隔着约30里。途中只零星长着些红柳、胡桐,一些枯树横陈在沙地上。他们找到的当地向导,进入沙漠后发现全然忘记了以前跟随外国探险队走过的路线,第二天便被解雇。黄文弼一行只能不时登上沙丘远望,循着沙碛铺成的若隐若现的道路,走一程看一程。
他们进入沙漠正值风沙凶猛的春季,时不时就起风沙。最严重的时候,“走沙扬尘,十步之内,即不见人”。沙漠里并非荒无人烟,也有当地人开辟的道路、挖的水井等踪迹,但这些踪迹若有似无,很容易迷失,黄文弼一行几乎每天都在迷路。他们一路走,一路向遇见的猎户、村民询问古代遗址,“沙漠湖滩,有古必访”,采集了许多陶片、铜钱、古文书残纸等古物。
经过这次“南河”追踪之旅,黄文弼根据现存断续的河床痕迹以及沿河遗存,判断其断流发生在5世纪至8世纪之间,这对于该地区古国和丝路兴衰等课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证据。
黄文弼的新疆考古,不仅在寻找古国与古城遗迹,也为解决关于西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找着线索。譬如这些西域古国兴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楼兰等西域诸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原关系的演变等。他考察了塔里木盆地诸多重要佛窟,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和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
虽然艰辛备至,一路上倒也不乏难得一见的美景。黄文弼在日记中记录过夜行:“月光如银,昏黑之中照耀着荒凉寂静的草滩。凉风漫漫吹来,骆驼一步一步随红灯行进。前面仿佛有人影,近视却是枯木;忽焉大山在旁,忽然变为云烟……”也记录过夜宿沙漠:“月在丛树林中,方腾腾而起,如婴儿之坠地,赧赧然欲出不出,亦沙漠佳景也。”
从田野回到书斋,另一段更漫长的苦旅在等待着他。
他要将所有考察的成果写成报告,为学界共享。但彼时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常常只能在颠沛流离中笔耕不辍。
1930年从新疆回到北平,他明确了“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库车,次和阗,次佉沙”的工作目标,蒲昌即罗布泊。他效率很高,1931年和1933年,他便根据考察所得,首先出版《高昌砖集》与《高昌陶集》,整理研究了从高昌古国出土的砖志和陶器。随后,他便繁忙起来。1934年起,他先后在安阳、洛阳、西安、南京等地进行考古工作,之后到西安主持修复碑林,只能晚上对随身携带的罗布泊考察采集品进行整理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机构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陕西城固,黄文弼担任历史系教授,同期受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39年至1942年间,战火纷飞的岁月,他奔波在川陕两地,一边教学,一边仍继续新疆考察报告的撰写,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
他在《高昌陶集》叙言中曾回顾那些年的动荡生活:“又适逢严重之国难,外寇侵陵,处于恐怖城中,手握校稿,目瞋飞机,自以为七年精血,将与炮弹以俱去矣。不料尚能许此书出版也,幸何如之!”
战争中印刷出版困难,《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出版耗费了不少时日,1948年终于面世时,黄文弼又慨叹:“十余年之苦心研究,终得与世人相见,何幸如之!”朱玉麒如今读到这些文字,看到这本无法复制的手稿命悬一线,能够得以保全并印出来,“想想都感到后怕”。
万般努力之下,黄文弼的考古成果依然没有幸免于战争的摧残。为躲避日军对西安的空袭,部分西北考察收集品被转移到汉口保存。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去汉口的英国洋行堆栈查访文物,寄存在此的大部分新疆收集品,已经毁于战火。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旦给予他时间和安稳,他便爆发出惊人的学术能量,《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隔不到4年先后面世。1958年,当《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时,黄文弼新疆考古的代表著作“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全部完成,历时26年。这位倔强而坚韧的学者,终于在纸面上将八万里足迹重新走过。
一次考古任务的完成,结束于报告的完成。黄文弼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新疆考古,也完成了他参与西北科考团的使命。
“如果没有献身学术的牺牲精神,这三记两集的报告可能在任何一次颠沛流离中胎死腹中。”朱玉麒说,“我们这个时代,大概不会遇到各种乱离岁月给写作报告带来的艰难困苦。”他从黄文弼身上读出一种“以命相搏的意志”。
“从尘封的历史中解放出来”
当黄文弼回到北平时,他已经成为当世不可忽略的重要考古学家。而3年前在西北科考团中肩负起考古重任时,他其实还是个新手,并没有实际的考古经验。现代考古学彼时刚刚进入中国,也很难找到有实际经验的人选。
此前一年,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展考古发掘,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而令中国考古声名鹊起的重大发现——安阳殷墟,要在西北科考团启程一年后才破土而出。往后,在中原地区不断冒出惊世发现之时,新疆考古在黄文弼的率领下,实则也同步出土着重要发现。在西北广漠的天地之中,黄文弼形单影只,踽踽独行,以“一个人的考古队”开疆拓土。
黄文弼既在追随也在追赶着国外学者的步伐。那些捷足先登的国外探险队,领衔的往往是经过学术训练的学者,比如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斯文·赫定等人。他们并未囿于书斋,而是有着过人的行动能力,这是他们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根本不同。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从中国考察回国后称,中国人的读书能力很强,但却不做野外考察。等到斯文·赫定四度来华,黄文弼等学者坐不住了,他们知道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在三尺书斋,也在辽阔的大地上。
民国时期,随着故纸堆之外的文化遗产逐步被重视,留学归国的学者也带回了西方的考古、地质、建筑、古生物等新兴学科,中国的读书人陆续走向田野。
李济、梁思永等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学者们从地下发掘出了河南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同仁在全国寻找、记录和保护古建筑……西北科考团不论在考察范围、学科跨度还是成果上,与其他几项更为知名的学术行动都足堪相提并论。然而在长达几十年中,西北科考团以及黄文弼、袁复礼等学者的成就,几乎被埋没了。直到现在,也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黄文弼中心副主任吴华峰说,正当黄文弼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学术事业也在散发余热之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变化已经悄然袭来。当时的学术环境也日趋恶劣,西北科考团成员基本上切断了一切对外的交流与联系,这些都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
作为对比的是,考察团外方成员回国后,从1937年起至1996年,先后出版了56卷《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斯文·赫定本人也写下了几十万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而参加科考团的中方团员前后15人,因为战乱和政治运动,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黄文弼锲而不舍写就的“三记两集”及其后人整理的论集和日记,成为科考团中出版成果最为充分的学者。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黄文弼的三本新疆考古记相继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但几十年后已经难以寻觅。等到1984 年,日本学者宫川寅雄准备翻译《黄文弼著作集》,向学者夏鼐请求代购“三记”时,作为黄文弼同事的夏鼐也无从购买。“三记两集”没有再版,但其中的《罗布淖尔考古记》1968年在日本影印出版,1988年香港也曾影印此书。2009年,线装书局将“三记两集”策划为《中国早期考古调查报告》第二辑,也按照初版原书影印出版,但数量偏少,寻觅不易。
即便黄文弼的著作没有再版,但影响力早已遍及海内外学界,始终是西北考古与研究者的必备书,后辈学者们通过电子版和影印版获取给养。新疆考古学的一位资深学者曾说,当年他们从事考古工作时,就是拿着黄文弼的著作在全疆各地跑,这些著作就是他们的领路人。
日本艺术考古学家前田耕作曾说:“黄文弼为了把案头的金石学转换为富有生机的田野考古学,已经苦苦行进了4万公里。把这样一个黄文弼从尘封了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大约就相当于把偏向西面来看中亚的观点,摇摆到从东面来观察。”在他看来,黄文弼以一己之力,将新疆乃至中亚考古和历史,变为中国的学问。
黄文弼的西北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可供发掘学术价值。例如“三记”中记载的出土文书,来源广泛、语种丰富,包括汉语在内,塔里木盆地出现过的10种历史语言几乎都有采集。朱玉麒认为,将近百年之后,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成果的丰富,这批“黄文弼文书”有值得重新汇总整理的价值。《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最近即将出版,是对黄文弼文书最完整的整理。
“黄文弼的著作是从事西北考古与研究者的案头书。因如此,三记两集的再版也受到学界的期盼与关注。”吴华峰说。他参与主持了此次再版“三记”的校勘,《罗布淖尔考古记》校勘条目有1300多条,但绝大多数是语言文字上的校正,科学记录和表述方式并没有多少需要改动的地方,经受住了时间检验。
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生前使用和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成立“黄文弼中心”,将“黄文弼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研究者们正分类整理西北科考团中方成员未经公布的大量文献,重新打捞那些尚未被充分利用过的学术资料,让中断的研究重新连接,让先驱的心血得到承托,让那次科考成果在百年后最终完成。
而黄文弼的生命早在1966年已经戛然而止,终年73岁。他已经编了目录的《西北史地论丛》和写了初稿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等著作都没有完成。12年后的197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为考古学家黄文弼、陈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颜訚三位学者举行了追悼会。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3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