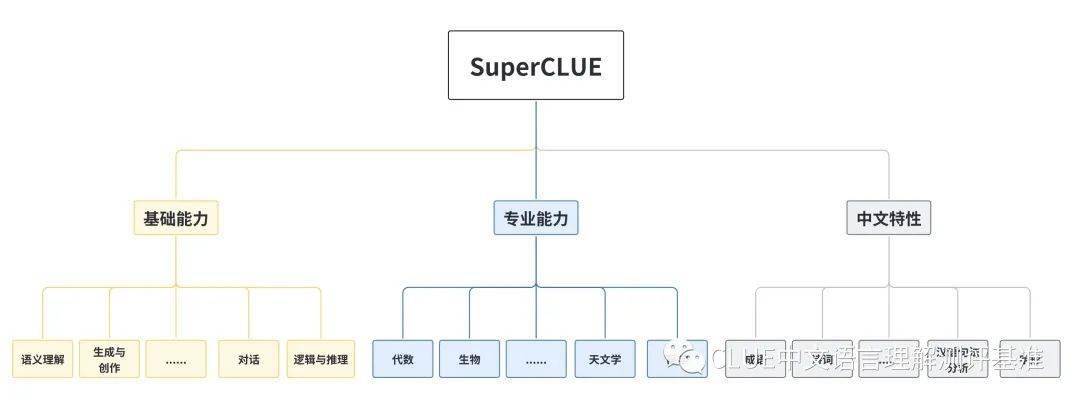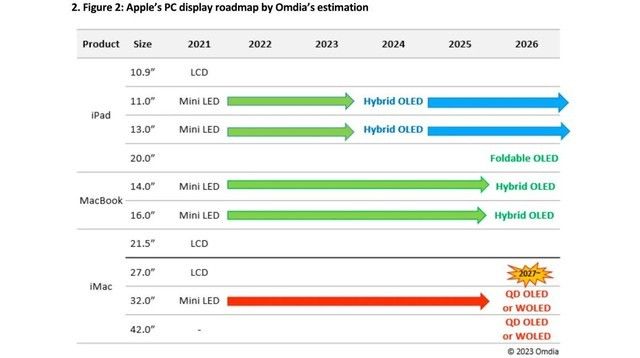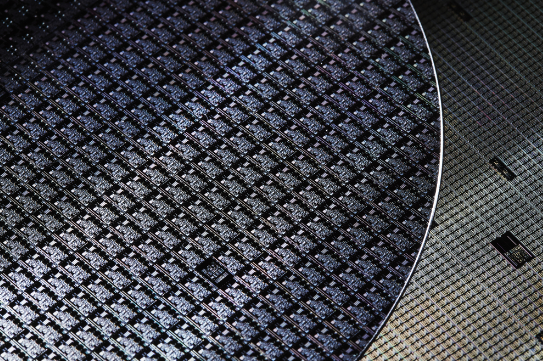【编书者说】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绵延至今,从未断绝。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中国古代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一大特色。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就是以文献为切入点研究文化,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文献,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是推动人类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贡献。实际上,早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简帛书写、金石镌刻等文献生产方式,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也确立了坚实深厚的文献历史传统。《尚书·多士》最早用文字记载确认了这一传统:“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古代文献数量极夥,以现存古籍文献(不包括出土文献)而言,即不下二十万种。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献类型十分丰富,除书本外,文书、卷子、档案、信札、石刻、契约、账册、书画等不一而足。中国古代文献在书写、制作、印刷与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吸引后人对中国古代文献史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时也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1.文献是人与物的交集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献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突出的文化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价值。狭义的文献一般指书籍或有文字、图像的载体,广义的文献外延较广,包括一切人类符号载体。文献是思想知识的载体,其根本属性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文献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以自身的内容记载传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质形式嵌入广义的文化史架构之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最早使用“文献”一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文献”这个词,明确指出:“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这是“文献”一词的经典解释。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文献”包括典籍与贤人两个方面。典籍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贤人是传承文化的主体,典籍与贤人亦即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切的揭示了文献的文化本质。环绕着文献的制作、生产、衍生、阅读、聚散、流通、使用等过程,各种社会群体与历史力量参与其间,纵横交错,在文化与文献之间形成无数交叉联结之点。经由这些联结点,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献现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献史所凸显的文化特性。这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首要着力的方向。
中西学术传统都很重视对于文献本身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书志学、藏书学等文献学相关学科,图书馆学、金石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也经常涉及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涵盖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等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来以整理图书为己任,尤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往圣继绝学,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文化学术的历史使命感。具体而言,校勘学揭示了古代书写与传播的方式与特点;目录学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思想源流;版本学揭示了文献的物质文化形态;典藏学揭示了文献聚散传承的轨迹及其社会文化因缘。它们都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文献资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更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随着20世纪初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轫,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文化自觉更加明显,其代表作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锡《古书通例》等。其后又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它们带动了一大批关于书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类研究仍然偏重于书籍物质形态本身,对文献的文化史意义的抉发不够深广,还谈不上系统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2.“书籍史”的文化观照及其不足
自20世纪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观照视角兴起以后,开始出现以社会、经济、文化取代传统历史编纂学叙事关注的倾向。文献,特别是书籍印刷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书籍史研究于是应运而生。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夫贺与马尔坦出版了《印刷书的诞生》,从宏观角度解答印刷术发明对整个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为书籍史研究导夫先路。20世纪中期以后,广义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明显,图书的阅读史、接受传播史、商品贸易史,特别是图书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作是美国史学家达恩顿所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以18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出版过程及其流通角度,探讨图书出版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历史。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书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将书籍的传播过程视为理解思想、社会以及历史的最佳途径及策略。
简而言之,西方学者的这些“书籍史”研究,不同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它是一种文化史的观照,其核心是将书籍理解为文化历史中的一股力量。书的制作情形如何,由谁制作,为谁制作,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为何,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书籍的出版,思想理念又如何通过书籍而传播,书的价格与书的贸易情况如何,书籍的传播与接受的社会效果如何,读者的阅读能力与参与性怎样,国家文化当局的权威及其影响力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意识的产生,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书籍史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这一学科的内涵是:在文献书籍存在的长久时段内,用最广泛、最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它,探究其社会功用、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关的文化实践与影响等等。
西方学者运用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学者在书籍史方面的探索。但西方学者主要关注近世以来的书籍与印刷,对其他时代其他形态的文献关注不足,亦较少利用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学术资源。结合中西学术积累进行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是一个极富意义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方向。
3.确立“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方向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经过十二年的辛勤耕耘,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终告完成。研究团队及其依托的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群体,在古典文献学、域外汉籍研究、古代文化史研究等领域已有较丰厚的学术积累,也较早开始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探索。
十卷本丛书包括:第一卷《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赵益撰);第二卷《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兴无撰);第三卷《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于溯撰);第四卷《宋代的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巩本栋撰);第五卷《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俞士玲撰);第六卷《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徐雁平撰);第七卷《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张宗友撰);第八卷《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撰);第九卷《汉籍东传与东亚汉文化圈》(金程宇撰);第十卷《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程章灿、许勇编撰)。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探寻这股力量如何发生作用、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如何形塑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总体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结构体系上,以问题为中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对文献文化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观照。全书的总体框架大致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榜样,绪论与专论相结合,既重视各卷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突出各自的专题性和独特性。每个子课题都设立核心焦点,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追求论述的深度和视角的创新。第二,具体操作上,简牍时代、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并重,在继续深入进行明清书籍史研究的同时,显著填补宋以前文献文化史的空白;在突出其历史阶段性的同时,突出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态多样性,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特别重视中国古代文献外传对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意义。第三,理论方法上,从原始文献出发,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兼收,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参证,考据与义理并重,总结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色,彰显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本书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在文献发掘、研究方法及学术思路上都力求突破创新。第一,重视发掘以往未受重视的文献类型,在传统的书籍文献之外,重视日记、书札、石刻与出土文献,重视国外的书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文献。第二,本书由多位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承担,以“长时段”的时间观念,弱化单纯的线性进程,各以一个较大问题为中心,如古代文献的核心问题、早期经典形成与文化自觉、中古时期历史制作与知识传播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多维度阐释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丰富内涵。第三,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学术思路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将文献与文化相互融合,从文献的实证角度阐释文化,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审视文献,突破了已有研究成果将文献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割裂的格局。换句话说,本书的研究突破了传统文献史研究的旧有框架,借鉴“书籍史”这一新文化史研究视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对象从“书籍”扩展至“文献”,时间范围从“宋元明清”扩展至整个文明史,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化历史内涵,特别注重发掘古代文献的文化建构意义。
相对于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领域,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只是扬帆初航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光明日报 作者:程章灿,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