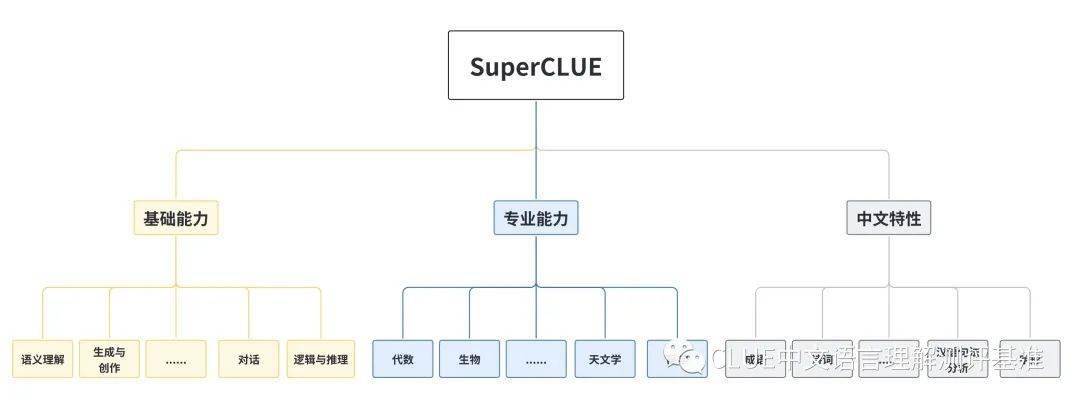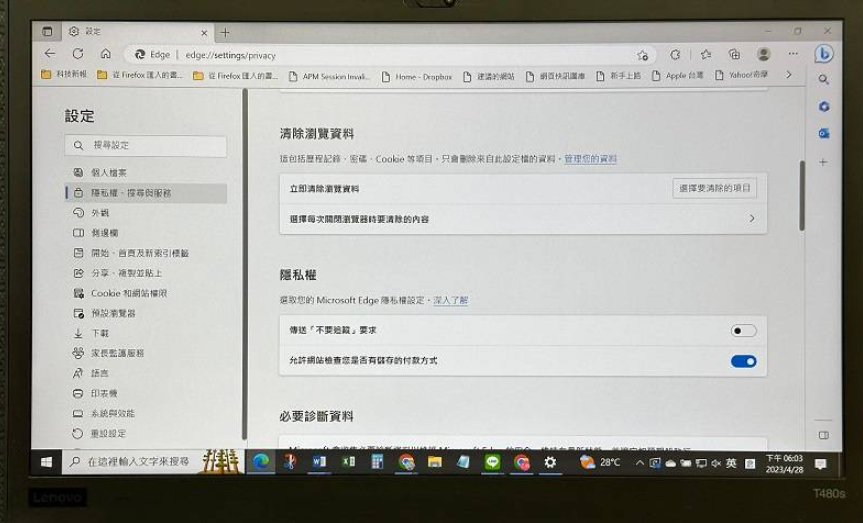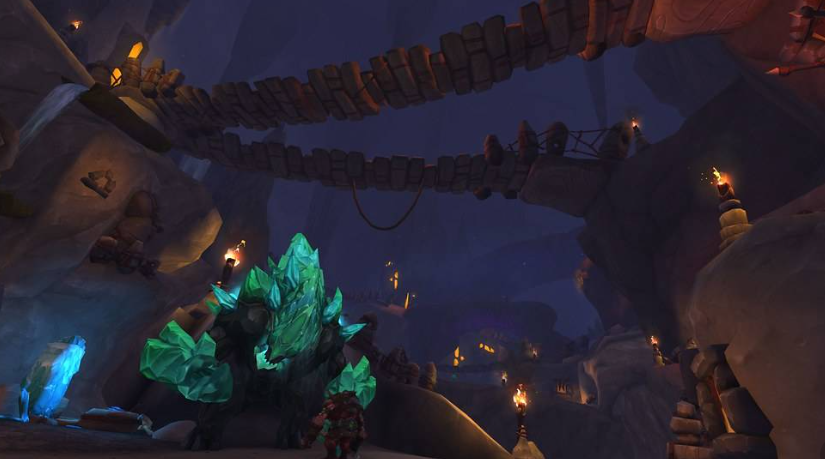【学人谈】
北宋宣和年间,宫廷画院的发展臻于顶峰,其创作成就与徽宗皇帝直接相关。赵佶在绘画题材上主要关注皇宫内院之物,正如宋代邓椿所著《画继》言其“独于翎毛,尤为注意”,而观《宣和画谱》所收花鸟画为各科之冠,“其自形自色,虽造物未尝庸心,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从中不难看出赵佶对于花鸟画的青睐程度。纵观徽宗时期的画院创作,花鸟画可谓熠熠生辉,赵佶的艺术观念也充分体现在这一画科上。抛开皇帝尝以古人诗句为试题选拔画家的逸闻佳话,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赵佶在画院创作中提倡形似与崇尚法度的事实,以及其在绘画中强调写实的严谨态度。
这一创作态度被贯彻于画院之中,造就了《画继》中所谓的“宣和体”。对形似与法度的追求必然以写生为前提,在这一点上赵佶传承了崔白、吴元瑜一派的艺术观念。如《芙蓉锦鸡图》用笔工细、设色艳丽,对锦鸡的刻画极为生动,显现出高超的写实技巧。画中锦鸡与蝴蝶相互呼应,别有生趣。由此可见,在师造化的基础上,赵佶对祖宗之法的变革并非彻底推翻先前精致富丽的画风,而是一改缺乏生趣的刻板描摹,使画面尽显鲜活、灵动之感。再观《梅花绣眼图》,画中梅枝瘦劲,疏花点点,玉蕊轻吐,一只绣眼鸟俏立枝头,顾盼四周,与清丽的梅花相映成趣。该作画面简洁却处处精致,画中所绘梅花为宫梅,精细纤巧且富贵高雅,代表了北宋宫廷的审美旨趣。
至徽宗朝,宋画在理论与实践上彻底摆脱了对隋唐五代时期的体制沿袭,而其全面自立则是借助于文人画的发展。徽宗时期,画院对写实风格极度追求,在对物象的细微观察上与文同等人在“格物穷理”的层面上颇为一致。从绘画本体语言及技巧发展上看,在赵佶对于具象写实的严苛要求下,宣和画院众工的创作达到了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极高水平。但如蔡绦所言:“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虽宣和年间供职于画院者甚众,但几无一人有作品传世,我们只能从那些或为画工代笔的画作中窥见“宣和体”之面貌。如《腊梅山禽图》显现出画家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写实程度之高可为院体工笔之典型。画面中线条工细、色调秀雅,用墨笔勾勒,再以水墨渲染,透溢出几分文人意韵。另外,北宋宫廷绘画在以妙笔刻画自然界动植物的同时,往往强调其灵性的凸显,以此展现自然的和谐之美。如《红蓼白鹅图》中的红蓼与白鹅对比鲜明,红蓼于水岸斜出,其后一只白鹅扭首曲颈梳理羽毛,神情灵动,逼真自然,与岸边花草互为衬托。该画在技法上粗笔勾勒与工笔细描兼施,色彩既朴素雅致又不失皇家贵气。其中红蓼的笔法相较略粗,设色有浓淡变化,表现了植物茎干的质感与色泽;白鹅的描绘极为精细,以白粉勾描翎羽,以浅黄填染鹅喙与蹼趾,造型精准;坡岸则以墨笔横扫,再随手点出杂草,富有简率之趣。
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指出,“现存的具名赵佶的画,面目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粗简拙朴和极为精细工丽的两种。”他以为赵佶的亲笔画“应属非院体的、比较简朴生拙一些的风格。”如《柳鸦图》以水墨为主,略施淡色,笔法古劲,风格特异,鸟身黝黑如漆,微露青光,极为稀见。此外,《竹禽图》中禽鸟以刻画精细而见功,正如《画继》记其绘珍禽时“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但画中崖石却用写意画法处理,用笔拙朴凝重,同《柳鸦图》极为相似。
由此观之,彼时的宫廷绘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而赵佶的创作清晰地显现出这种两面性。审美取向的双重标准并未造成宫廷绘画的内部冲突,徽宗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北宋皇室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赵佶能够在水墨领域有所抒发,如《池塘晚秋图》纯以水墨为之,虽笔法写意但造型写实,符合徽宗风格。只是这种墨戏仅限于宗室间的自娱,从装点宫室这一实际需求出发,赵佶其实并不允许放逸之气浸染画院,正如《画继》所言,“至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
北宋画院在徽宗的全面主持下,其创作规模与制作水平堪称极盛。不得不说,北宋宗室文人化的成功使其走上了纵情书画的道路,宗室画家的文人思致及其对文人画观点的认同,使得北宋后期的宗室绘画与文人画的创作发展几乎是并行的。北宋后期,皇室对于画作的玩味逐渐发展到极致,虽然画院创作与后起之文人画理念存在差异,但这种情况在徽宗朝却不是一种矛盾的存在。
随着宋室南迁,由宣和画院入绍兴画院者不在少数。南宋临安绘画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北人的徙入息息相关,而徽宗皇帝与宣和画院的审美取向亦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南宋宫廷绘画的发展。
(光明日报 作者:赵振宇,系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田博群】